
马伯庸已经记不清自己是第几次来南国书香节了,但是每次迎接他的,都是大排长龙的读者。8月17日,在新书《桃花源没事儿》分享会上,马伯庸笑称,广东是他的福地。从《食南之徒》到《长安的荔枝》,马伯庸笔下的故事都跟岭南有关。“未来我会继续创作和广东有关的文化作品,也会每年来广东跟大家见面。”
新作留住了我的人生年轮
作为近年来备受瞩目的作家,马伯庸的作品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和对历史的深刻挖掘而广受好评。从《长安十二时辰》到《长安的荔枝》,多部作品被改编为影视作品,引发收视热潮。他幽默风趣的语言风格和细腻的笔触,总能让读者在细节和伏笔中收获知识与启发。
《桃花源没事儿》是马伯庸畅销书系“见微”历史短小说第三部作品,前面两部作品《长安的荔枝》《太白金星有点烦》在豆瓣网评分8.75,数百万读者热烈认证:堪称打工人嘴替文学天花板。

活动现场,马伯庸分享了新书创作背后的故事。《桃花源没事儿》讲述了一个天生穷命的小道士玄穹在桃花源打工的日常。以妖喻人,以幻写实。正如这本书所表达的,每个人的成长都是不断突破自我的旅程,书中狐狸婴宁的“金锁”、小道士的“命格”如此,现实中困于职场、为自我怀疑所束缚的我们亦如此。
“若单纯以动笔时间和停笔时间来衡量的话,这本书是我写得最长的一本,没有之一。”这个故事萌生于2013年,那时候作者还是一个白天上班、晚上写稿,顺便给新生儿换尿布的状态。而灵感来自于遛弯时在小区门口遇到的片儿警老刘。
老刘给马伯庸讲了段子:“附近有个小饭馆,消防通道总是堆放杂物,怎么教育都屡教不改。后来有个道长路过,说你这风水不对,挡了财运,老板连夜就给清干净了。”讲完逗得他哈哈大笑,他想如果有个道士管理居民区应该也挺有趣的。
这个想法从此在他心里生了根,直到偶然间看到了汪曾祺改写的《聊斋志异》和古龙的《七杀手》,故事终于慢慢长出了枝丫。不当一个紧迫的任务,纯粹作为一项休闲游戏,一晃十几年,断断续续,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竟然在2024年诞生了。
“因为它的创作时间实在太长了,以至有意无意中,也保留了我这十多年来心境变化的痕迹……让它保持着这种斑驳的风貌,就当是留住了我的人生年轮。”马伯庸说。

希望看到更多写古代广东的文艺作品
最近,影视剧《长安的荔枝》热度居高不下。活动现场,马伯庸告诉读者,他在电影里客串了一个小角色,披上了红袍,成了个官员,还亲自给自己写词儿,跟刘德华演的杨国忠有板有眼地对戏。“我还打电话给我妈妈,说你儿子出息了,跟刘德华同台飙戏。”
不管是《长安的荔枝》,还是《食南之徒》,马伯庸都把写作的焦点投向古代的广东。
马伯庸表示,他很喜欢历史中的古代广州,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各种文明交汇之处,是一个巨大的商贸中心。今年南国书香节主打国际化,有这么多外版图书走进来,同时也有中国文化的输出,实际上是我们软实力的最好体现。
在马伯庸看来,文艺作品最重要的功能是启发年轻人的兴趣,让他们愿意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入挖掘,以此为入门,进行更深的开拓。“比如说我前年出的《食南之徒》出版之后,就听说很多人会跑到南越王博物院去打卡,甚至有些人会因此喜欢上广东古代历史,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例证。”

他发现,不管是影视剧,还是文学作品,岭南地区的古代体现得很少,大家的注意力都在近代的广东,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作品让大家关注古代的岭南文化。因为广东历史非常悠久,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色,他也希望以后能够看到更多的关于古代广东的作品。
马伯庸强调,不管时代怎么变,总有一小撮人在关注文学,因为人类的表达和倾听是基本的需求,这种需求很难用别的东西代替。“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,文学的意义不在于给我们多大的激励,但是在我们受挫、沮丧的时候,文学能够给到我们托底的力量。它就像混乱时代的桃花源,停车场里的一辆汽车,给我们提供了精神庇护的空间,始终伴我们左右,所以我对文学还是很有信心的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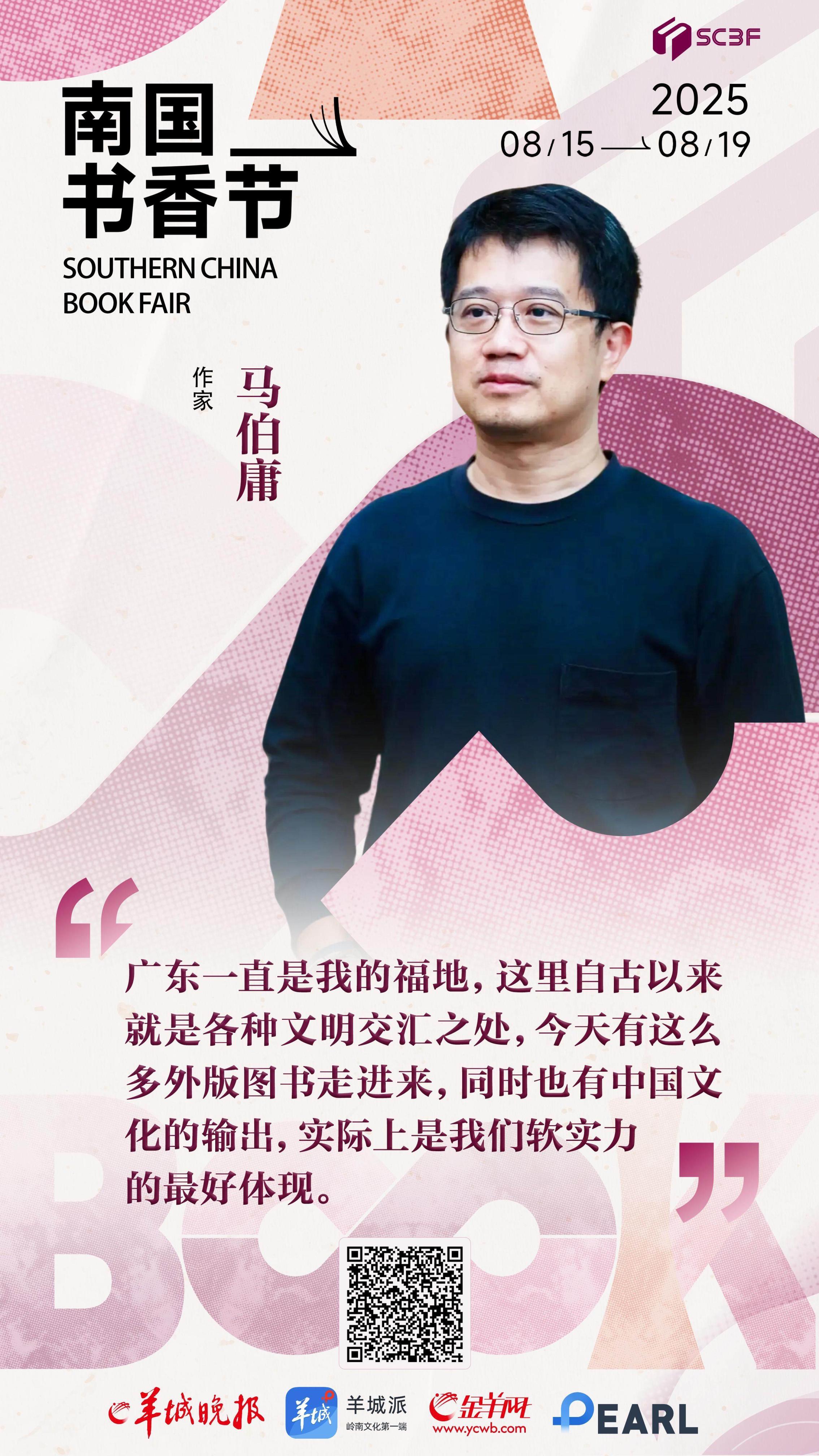
更多热点速报、权威资讯、深度分析尽在北京日报App
作者:孙磊 周欣怡 邓鼎园 梁岚 李论
聚富配资-炒股杠杆平台排行榜-实盘10倍杠杆-股票配资开户多少钱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


